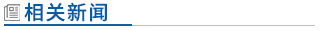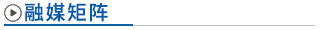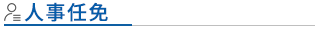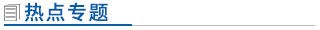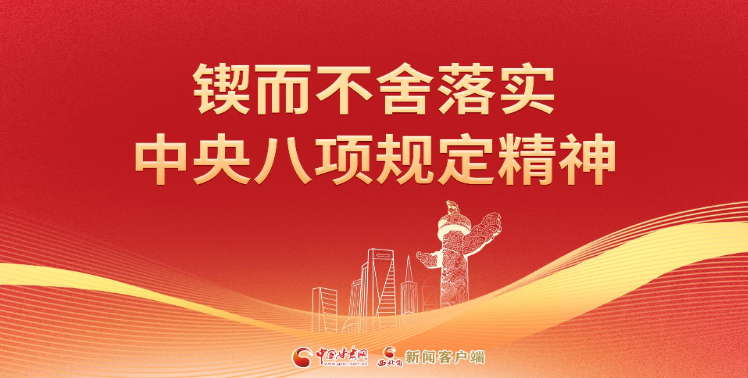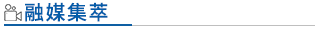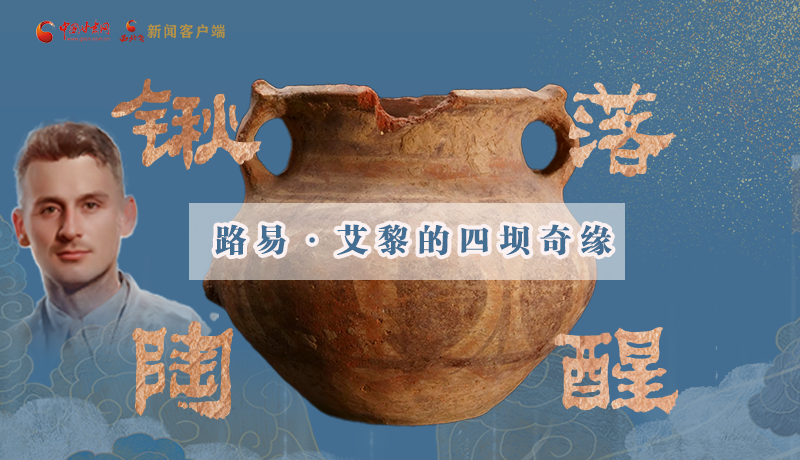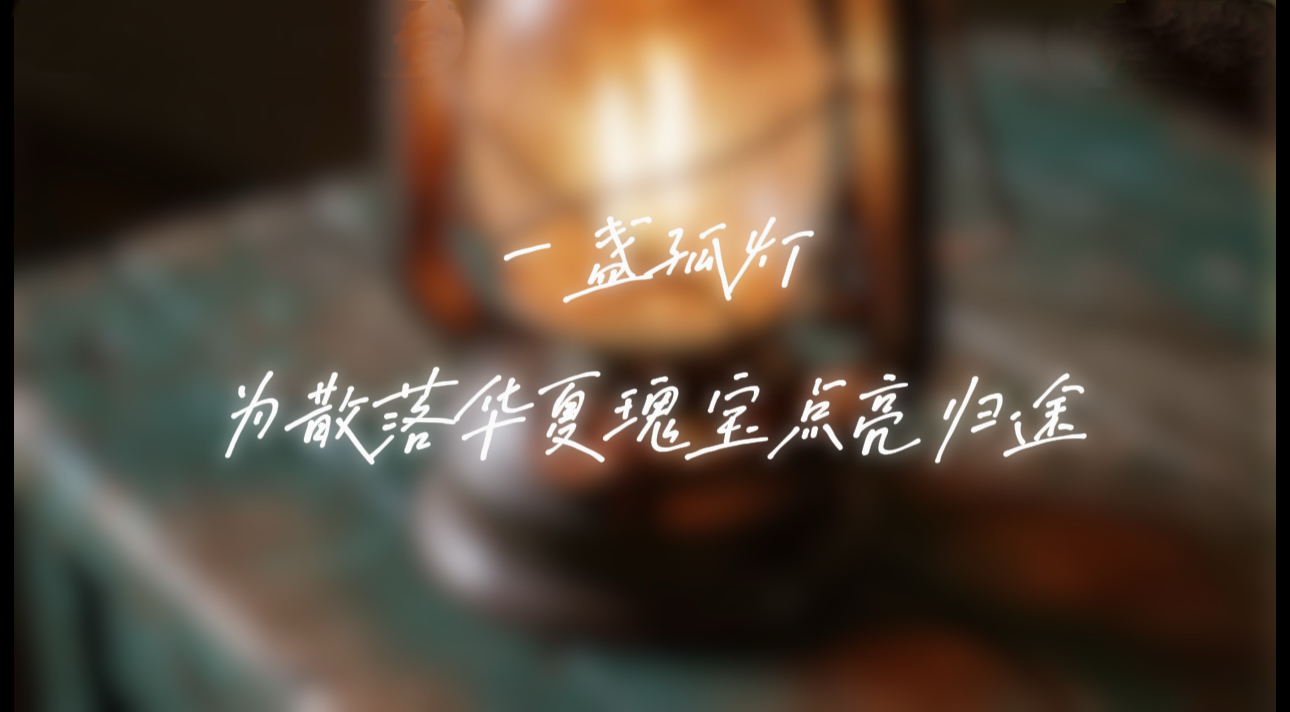原標題:網絡服務者過度收集個人信息違法
受邀嘉賓:甘肅策橫律師事務所律師阮 磊
主持人:新甘肅·甘肅法治報記者李曉云
本期主題:在數字化浪潮席卷生活的今天,手機應用已成為我們獲取信息的重要工具。然而,當使用各種App時被強制索取手機號,是否侵犯了我們的合法權益?本期“舉案說法”結合典型案例和民法典有關規定解讀這一法律問題。
典型案例:某公司系某詞典App的開發者和運營者。馬某下載后使用該App時,系統提示用戶需閱讀隱私政策。隱私政策中載明需要收集電話號碼等個人信息。若用戶在未實際閱讀的情況下點擊手機屏幕其他位置,該提示內容即消失并自動勾選“已閱讀并同意隱私政策”選項,且勾選后沒有撤回同意的途徑。若用戶點擊拒絕,則App自動退出,不向用戶提供任何服務。馬某認為,該App強迫或者變相強迫自己接受隱私政策,收集手機號等屬于過度收集個人信息,構成對自己個人信息權益的侵害,故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某公司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并賠償維權合理開支等。
裁判結果:法院審理認為,網絡服務提供者應基于個人同意處理個人信息,其預先擬定的有關個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協議應使個人充分知情,并自愿、明確作出同意。該App的基本功能為詞匯查詢,用戶的手機號碼并非使用詞匯查詢功能所必需的信息,故某公司存在過度收集用戶信息的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規定,構成對馬某個人信息權益的侵害。本案訴訟過程中,某公司已對該App的隱私政策進行了修改并新增撤回同意等功能。法院判決:某公司刪除其收集的馬某手機號等個人信息,向馬某賠禮道歉并賠償其維權合理支出。
主持人:法院為何認定收集手機號屬于“過度收集個人信息”?
阮 磊:“過度收集個人信息”在法律意義上即超過了“采取對個人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并“限于實現處理目的的最小范圍”。本案中,某公司作為詞典App運營方,其強制要求用戶提供手機號碼,明顯超出了“實現處理目的的最小范圍”。即便企業辯解手機號用于“提升服務”或“安全驗證”,也需證明目的是為了實現核心功能所必需且不可替代。但是,該公司既未在隱私政策中明示手機號的具體用途,亦無法證明其與查詞功能存在實質關聯,屬于典型的“寬口徑收集”。而且,企業完全可以在技術上通過設備標識符(如匿名ID)或郵箱等對隱私侵入性更低的方式實現基礎服務,但其選擇強制收集敏感度更高的手機號,實質上是對用戶選擇權的剝奪。因此,某公司的行為屬于“過度收集個人信息”。
主持人:App設置“不勾選同意就強制退出”是否合法?
阮 磊:《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六條規定,個人信息處理者不得以個人不同意處理其個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為由,拒絕提供產品或者服務;但是,處理個人信息屬于提供產品或者服務所必需的除外。本案中詞典App的“捆綁式同意”設計,違反了“自愿同意”的核心原則。App通過界面設計(自動勾選同意、點擊空白處即默認同意)剝奪了用戶閱讀和決策的機會,屬于典型的“變相強迫”,導致用戶同意完全喪失法律效力。法律僅允許企業在服務核心功能所不可或缺時(如網約車App必須收集位置信息才能派單),方可拒絕向不同意收集的用戶提供服務。本案中,手機號與查詞功能并無必然聯系,App將“同意隱私政策”作為使用前提,同時也侵害了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故App設置“不勾選同意就強制退出”屬于不法行為。
主持人:若App未提供“便捷地撤回同意”的途徑會面臨什么法律后果?
阮 磊:《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所規定的撤回權是個人信息控制權的核心體現,確保用戶在信息處理失控時能及時止損。用戶撤回同意后,企業繼續處理個人信息即構成“無合法依據處理”。本案中由于撤回通道缺失,App對手機號的持續存儲和使用均轉化為持續性侵權,這正是法院判決“刪除信息”的直接依據。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六十六條規定,拒不改正違法處理行為的企業將面臨高額罰款(最高五千萬元或年營業額5%),甚至停業整頓的法律后果。
- 2025-07-02這場警校聯動反詐直播干貨滿滿
- 2025-07-02積石山交警開展交通安全宣傳教育活動
- 2025-07-02積石山縣開展“放假第一課”法治教育進校園活動
- 2025-07-02臨潭公安開展主題禁毒宣傳活動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