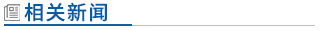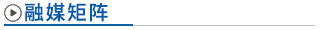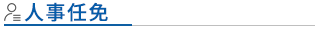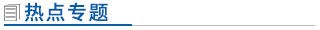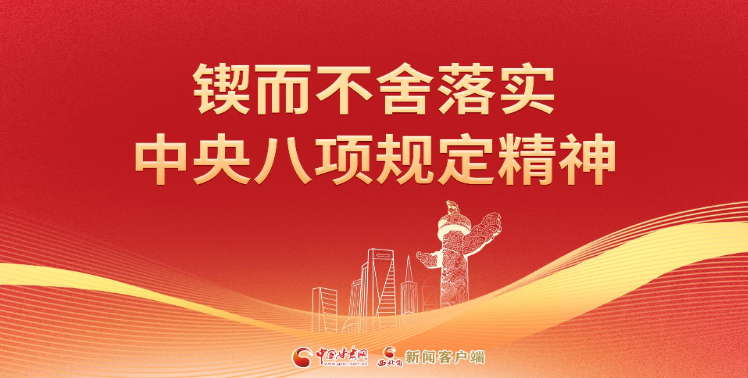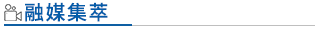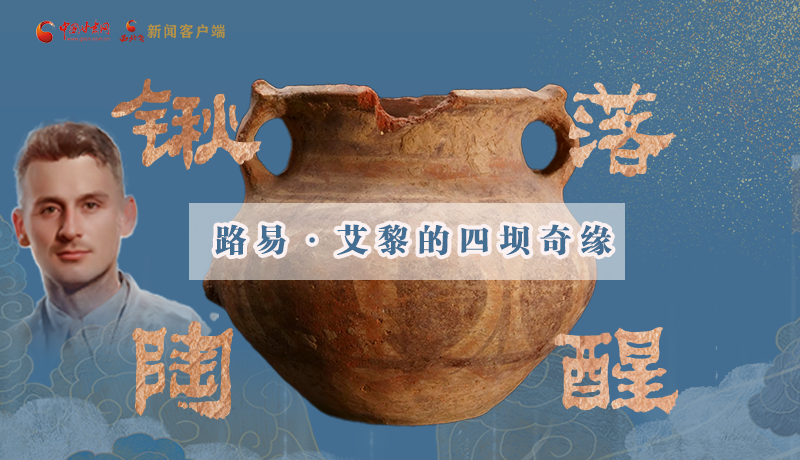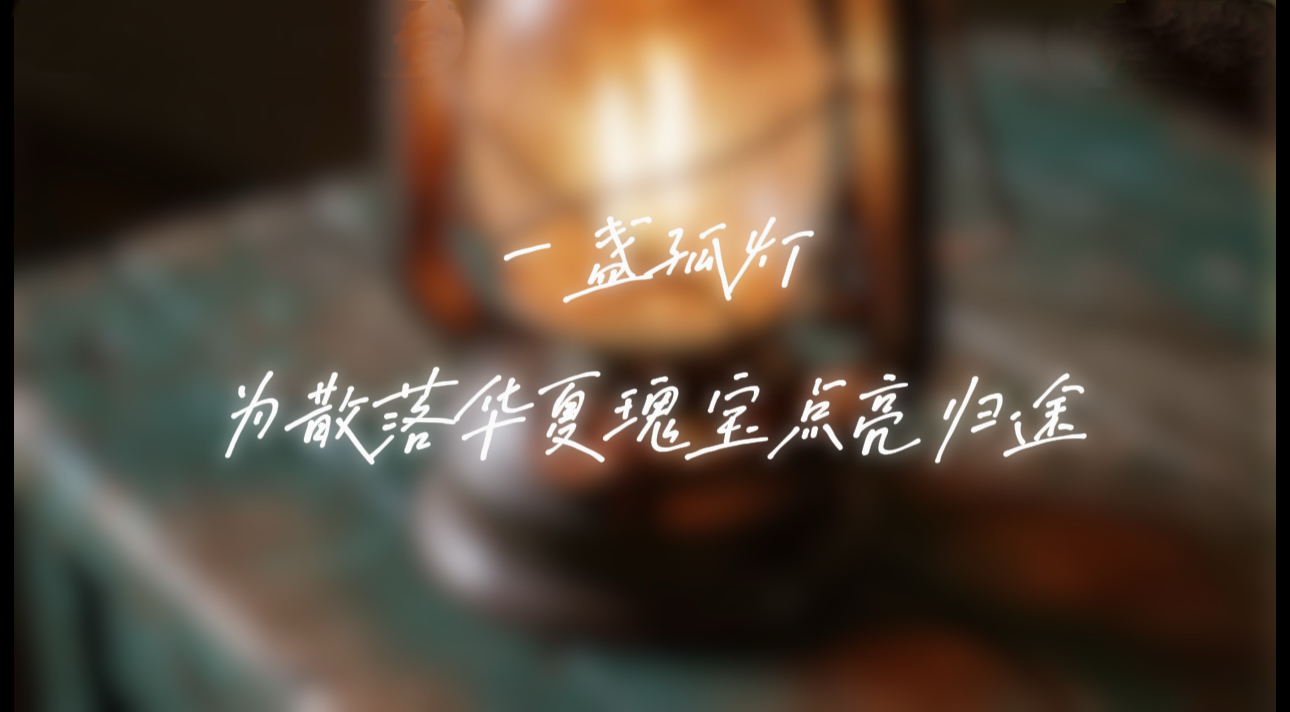【內(nèi)容提要】
對于刑法第九十三條規(guī)定的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來說,應(yīng)當(dāng)以是否從事公務(wù)作為能否將其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標(biāo)準(zhǔn)。村干部在拆遷工作中,既可能協(xié)助政府從事公務(wù),也可能僅僅從事村務(wù)管理。拆遷工作中,若村干部利用職務(wù)便利實(shí)施侵占拆遷補(bǔ)償款行為,觸犯的罪名也會(huì)有所不同,有的構(gòu)成貪污罪,有的構(gòu)成職務(wù)侵占罪,區(qū)分這兩個(gè)罪名,關(guān)鍵在于判斷實(shí)施違法犯罪時(shí)行為人的主體身份、所利用的職務(wù)便利以及侵占的財(cái)物性質(zhì)。
【基本案情】
案例一:2010年12月,A鄉(xiāng)B村開展拆遷騰退工作。經(jīng)A鄉(xiāng)黨委決定,B村黨支部書記甲任騰退安置指揮部騰退組組長,負(fù)責(zé)B村人口和宅基地面積的認(rèn)定工作。A鄉(xiāng)武裝部部長乙系本次拆遷工作負(fù)責(zé)人。甲與乙對B村人口和宅基地面積認(rèn)定材料具有審核權(quán)限。2011年,甲發(fā)現(xiàn)拆遷地域內(nèi)存在若干間本應(yīng)已經(jīng)拆除、不在此次拆遷范圍的空房,向乙匯報(bào)此事后,二人商定,由甲虛構(gòu)材料、安插社會(huì)人員到空房內(nèi),二人審核通過后騙取拆遷補(bǔ)償款,用以補(bǔ)充B村集體資產(chǎn),B村“兩委”其他成員對此不知情。后甲使用4名親友身份信息虛構(gòu)人口及宅基地面積認(rèn)定材料,共騙取拆遷補(bǔ)償款500余萬元。甲收到該筆錢款后并未上交村委會(huì),而是私自支配使用,乙對此不知情。
案例二:2011年7月,C鄉(xiāng)D村開展拆遷騰退工作。經(jīng)C鄉(xiāng)黨委決定,D村黨支部書記丙任拆遷騰退辦公室后勤保障組負(fù)責(zé)人,負(fù)責(zé)D村拆遷中的后勤保障工作。同時(shí),拆遷騰退辦公室下設(shè)定向安置組,負(fù)責(zé)D村人口及宅基地面積認(rèn)定工作,丙不在該組之內(nèi)。根據(jù)拆遷工作安排,D村村委會(huì)在前期工作中協(xié)助本村村民準(zhǔn)備人口和宅基地面積認(rèn)定的相關(guān)材料。
2010年,為解決D村部分無宅基地村民的住房需求,經(jīng)村民代表大會(huì)決議,村委會(huì)籌資建設(shè)50余間保障房分配給困難村民。保障房也在本次拆遷范圍內(nèi),保障房參照正規(guī)宅基地進(jìn)行補(bǔ)償,由D村村委會(huì)為保障房村民出具人口及宅基地證明材料,拆遷補(bǔ)償款歸相應(yīng)村民個(gè)人所有。對于尚未分配的保障房,作為集體資產(chǎn)參與拆遷,拆遷補(bǔ)償款歸村集體所有。2011年7月,拆遷工作開始后,丙接受親友丁等3人和其特定關(guān)系人戊的請托,為幫助上述人員獲得拆遷補(bǔ)償,明知上述人員不具備保障房分配資格,仍違規(guī)為其分配并出具虛假人口和宅基地證明材料。最終,丁等3人獲得拆遷補(bǔ)償款500余萬元,戊獲得100余萬元。
【分歧意見】
上述案例中,如何認(rèn)定甲和丙騙取拆遷補(bǔ)償款的行為性質(zhì),存在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rèn)為:案例一中,甲與乙共謀騙取拆遷補(bǔ)償款補(bǔ)充村集體資產(chǎn),虛構(gòu)人口及宅基地面積認(rèn)定材料并違規(guī)審核通過,騙取500余萬元拆遷補(bǔ)償款,構(gòu)成濫用職權(quán)罪共同犯罪。同時(shí),二人騙取的拆遷補(bǔ)償款,本意是補(bǔ)充村集體資產(chǎn),甲利用作為黨支部書記的職權(quán),違規(guī)占有該筆資金,構(gòu)成職務(wù)侵占罪。案例二中,丙利用拆遷工作中的職權(quán),為丁等3人出具虛假的人口和宅基地面積證明材料,造成拆遷補(bǔ)償款損失500余萬元,構(gòu)成濫用職權(quán)罪。同時(shí),丙利用職權(quán)幫助其特定關(guān)系人戊騙取拆遷補(bǔ)償款100余萬元,構(gòu)成貪污罪。
第二種意見認(rèn)為:案例一中,甲協(xié)助政府在拆遷工作中負(fù)責(zé)人口和宅基地面積認(rèn)定和一定審核工作,其利用從事公務(wù)的職務(wù)便利,虛構(gòu)材料騙取拆遷補(bǔ)償款500余萬元,構(gòu)成貪污罪。乙雖與甲共謀騙取拆遷補(bǔ)償款,并違規(guī)審核通過虛假材料,但其主觀上是用以補(bǔ)充村集體資產(chǎn),沒有非法占有拆遷補(bǔ)償款的故意,應(yīng)以濫用職權(quán)罪論處。案例二中,丙與丁、戊等人對非法占有未分配保障房對應(yīng)拆遷補(bǔ)償款形成共謀,并利用職權(quán)幫助丁、戊等人獲取600余萬元拆遷補(bǔ)償款。這一過程中,丙利用的是其作為村黨支部書記的職務(wù)便利,侵占的財(cái)物亦是本屬于村集體的拆遷補(bǔ)償款。對丙等人應(yīng)以職務(wù)侵占罪的共犯論處。
【意見評析】
本案中,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村干部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判斷
村干部是村基層組織成員的簡稱,主要是指村民委員會(huì)、村黨支部委員會(huì)成員。根據(jù)我國村民委員會(huì)組織法相關(guān)規(guī)定,村民委員會(huì)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wù)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因此,一般情況下,村干部從事的是管理村集體事務(wù)等相關(guān)工作,不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規(guī)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wù)的人員”,此時(shí)其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但是在特定情況下,村干部也可以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根據(j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ì)常務(wù)委員會(huì)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村民委員會(huì)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協(xié)助人民政府從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時(shí):(一)救災(zāi)、搶險(xiǎn)、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jì)款物的管理;(二)社會(huì)捐助公益事業(yè)款物的管理;(三)國有土地的經(jīng)營和管理;(四)土地征收、征用補(bǔ)償費(fèi)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繳稅款;(六)有關(guān)計(jì)劃生育、戶籍、征兵工作;(七)協(xié)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wù)的人員”,也即國家工作人員。
根據(jù)刑法第九十三條的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分為三類:一類是國家機(jī)關(guān)中從事公務(wù)的人員;一類是國有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人民團(tuán)體中從事公務(wù)的人員和國家機(jī)關(guān)、國有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社會(huì)團(tuán)體從事公務(wù)的人員;還有一類就是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wù)的人員。不論是哪一類國家工作人員,其共同點(diǎn)都是“從事公務(wù)”。即使是在國家機(jī)關(guān)中工作的人員,如果其所承擔(dān)的具體工作不屬于公務(wù)活動(dòng),仍然不能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對于刑法第九十三條規(guī)定的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來說,應(yīng)當(dāng)以是否從事公務(wù)作為能否將其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標(biāo)準(zhǔn)。
“公務(wù)”按照一般理解是指公共事務(wù),按照其性質(zhì)可以分為國家事務(wù)和集體事務(wù)。國家事務(wù)是指為了實(shí)現(xiàn)國家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jì)、文化等職能而進(jìn)行的組織、領(lǐng)導(dǎo)、監(jiān)督、管理活動(dòng)。集體事務(wù)是指集體組織內(nèi)部事務(wù)的組織、領(lǐng)導(dǎo)、監(jiān)督、管理活動(dòng)。刑法第九十三條規(guī)定的公務(wù)是指國家事務(wù),而不包括集體事務(wù)。
準(zhǔn)確理解“依照法律從事公務(wù)”的含義,對于正確適用刑法的有關(guān)規(guī)定至關(guān)重要。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和第二百七十一條分別規(guī)定了貪污罪和職務(wù)侵占罪,貪污罪中,犯罪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犯罪對象是公共財(cái)物;職務(wù)侵占罪中,犯罪主體為公司、企業(yè)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犯罪對象為本單位財(cái)物。兩罪在客觀方面均含有利用職務(wù)便利非法占有財(cái)物行為,關(guān)鍵區(qū)別在于主體身份不同,所利用的職務(wù)便利不同,以及侵占財(cái)物性質(zhì)不同。區(qū)分“公務(wù)”與“村務(wù)”,除了行為人的主體身份之外,更應(yīng)該結(jié)合具體案情,從行為實(shí)質(zhì)去把握。
二、案例一中,甲利用從事公務(wù)的職務(wù)便利騙取拆遷補(bǔ)償款,構(gòu)成貪污罪
案例一中,A鄉(xiāng)黨委任命甲為拆遷安置指揮部騰退組組長,明確賦予其負(fù)責(zé)人口和宅基地面積認(rèn)定和一定審核職權(quán)。甲負(fù)責(zé)的人口和宅基地面積認(rèn)定工作是行使A鄉(xiāng)黨委賦予的公權(quán)力,屬于協(xié)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在拆遷工作中,甲虛構(gòu)人口和宅基地面積認(rèn)定材料并伙同乙審核通過后騙取拆遷補(bǔ)償款,均是利用其協(xié)助政府從事公務(wù)的職務(wù)便利。此時(shí),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甲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有觀點(diǎn)認(rèn)為,甲在B村拆遷騰退工作中雖然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但其與乙達(dá)成的合意是騙取拆遷補(bǔ)償款后交給村集體,甲私自將拆遷補(bǔ)償款據(jù)為己有,利用的是其作為村黨支部書記的職務(wù)便利,并非從事公務(wù)的職務(wù)便利,因此不構(gòu)成貪污罪。其與乙共謀騙取拆遷補(bǔ)償款構(gòu)成濫用職權(quán)罪共犯,甲非法占有該筆拆遷補(bǔ)償款構(gòu)成職務(wù)侵占罪。筆者不贊成此觀點(diǎn)。
首先,從甲利用的職務(wù)便利看。貪污罪中的“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務(wù)上主管、管理、經(jīng)手公共財(cái)物的權(quán)力及方便條件。對于村干部協(xié)助政府在拆遷騰退中是否“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刑事審判參考》第1623號(hào)案例史某某貪污案裁判理由認(rèn)為,要“把握國家工作人員從事公務(wù)這一本質(zhì)屬性來認(rèn)定。具體來說,是要確定該村干部對拆遷補(bǔ)償款是否具有一定占有或一定意義上的支配權(quán)利,或?qū)Σ疬w補(bǔ)償款的發(fā)放是否起到一定的作用”,并列舉了幾個(gè)參考標(biāo)準(zhǔn),如,“村干部在人民政府組建的拆遷工作小組等代表人民政府履行職務(wù)的部門中是否擔(dān)任一定實(shí)質(zhì)性的職務(wù)”“在決定拆遷補(bǔ)償款發(fā)放的主要事項(xiàng)、主要材料、主要會(huì)議上,村干部的意見是否起到關(guān)鍵的作用”。案例一中,甲協(xié)助政府負(fù)責(zé)拆遷補(bǔ)償款的發(fā)放對象、宅基地面積認(rèn)定及一定審核工作,其認(rèn)定和審核結(jié)果對拆遷補(bǔ)償款的發(fā)放具有實(shí)質(zhì)性關(guān)鍵作用,因此,其騙取拆遷補(bǔ)償款的行為屬于利用了從事公務(wù)的職務(wù)便利。
其次,從犯罪對象看,甲套取的是公款,而非村集體資產(chǎn)。案例一中的相關(guān)空房不在此次拆遷范圍,本就不應(yīng)獲得拆遷補(bǔ)償款。即使甲、乙的合意是套取公款補(bǔ)充村集體資產(chǎn),但該筆拆遷補(bǔ)償款并未實(shí)際交付給B村村委會(huì),因此不屬于村委會(huì)的現(xiàn)存資產(chǎn)。同時(shí),雖然甲、乙形成將該筆拆遷補(bǔ)償款交付給村委會(huì)的合意,但屬于二人私下溝通,B村“兩委”其他成員對此不知情,且未經(jīng)過相關(guān)法定程序,B村村委會(huì)并無合法獲得該筆拆遷補(bǔ)償款的依據(jù),因此該筆拆遷補(bǔ)償款亦不屬于村委會(huì)的預(yù)期收益。綜上,該筆拆遷補(bǔ)償款不屬于村集體資產(chǎn)。所以甲支配該筆拆遷補(bǔ)償款時(shí)并未利用其村黨支部書記的職務(wù)便利。因此,甲騙取拆遷補(bǔ)償款利用的是其協(xié)助政府從事公務(wù)的職務(wù)便利,應(yīng)以貪污罪論處。
三、案例二中,丙幫助丁、戊等人獲得拆遷補(bǔ)償款利用的不是從事公務(wù)的職務(wù)便利,不構(gòu)成貪污罪,應(yīng)認(rèn)定構(gòu)成職務(wù)侵占罪
首先,從丙利用的職務(wù)便利看。丙在拆遷工作中任后勤保障組負(fù)責(zé)人,負(fù)責(zé)后勤保障工作。其違規(guī)為丁、戊等人分配村集體保障房,并為上述人員出具虛假人口和宅基地證明材料,顯然不屬于利用在后勤保障組從事后勤保障工作的職務(wù)便利。雖然D村村委會(huì)在拆遷前期工作中協(xié)助村民準(zhǔn)備人口和宅基地面積認(rèn)定的相關(guān)材料,但這并不能看作D村村委會(huì)從事了行政管理事務(wù)。一方面,C鄉(xiāng)經(jīng)過決策程序組建了定向安置組,賦予其人口和宅基地面積認(rèn)定的職權(quán)。D村村委會(huì)僅是協(xié)助村民準(zhǔn)備材料,后續(xù)的認(rèn)定仍由定向安置組負(fù)責(zé)。另一方面,D村村委會(huì)作為自治組織,管理本村的人口和宅基地屬于其自治范疇內(nèi)事務(wù),因此其協(xié)助村民準(zhǔn)備材料的行為,系D村村委會(huì)管理村務(wù)的行為。
其次,從丙幫助他人侵占的財(cái)物性質(zhì)看。第一,D村的保障房是2010年該村為解決部分無宅基地村民的住房需求,經(jīng)村民代表大會(huì)決議而建,在這次拆遷工作中,保障房也在拆遷范圍內(nèi),保障房參照正規(guī)宅基地進(jìn)行補(bǔ)償。對于尚未分配的保障房,作為集體資產(chǎn)參與拆遷,拆遷補(bǔ)償款歸村集體所有。也就是說,未分配的保障房對應(yīng)的拆遷補(bǔ)償款屬于集體資產(chǎn)應(yīng)入賬的預(yù)期收益。未分配的保障房與相應(yīng)的拆遷補(bǔ)償款,均屬于村集體資產(chǎn)。丙違規(guī)處置未分配的保障房的行為本質(zhì)上是對集體資產(chǎn)的處置。因此,案例二中,公款并無損失,丙也不存在侵吞、竊取或騙取公款的故意和行為。第二,丙幫助丁、戊等人獲得拆遷補(bǔ)償款的過程中,存在兩個(gè)行為。先是丙違規(guī)為丁、戊等人分配保障房的行為,后是丙為上述人員出具虛假的人口和宅基地證明材料的行為,僅有其中任何一個(gè)行為,都不足以騙取村集體的拆遷補(bǔ)償款,這兩個(gè)行為的目的均為丙幫助他人套取本屬于村集體的拆遷補(bǔ)償款。從本質(zhì)上看,導(dǎo)致丁、戊等人獲得拆遷補(bǔ)償款的原因系丙違規(guī)處置集體資產(chǎn)的行為。在這一過程中,丙并無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利用的是其作為村黨支部書記的職務(wù)便利,與丁、戊等人共謀違規(guī)侵占的是村集體資產(chǎn),應(yīng)以職務(wù)侵占罪共同犯罪論處。在丙等人共同實(shí)施的職務(wù)侵占罪中,據(jù)為己有并不要求丙本人親自占有,共犯中的丁、戊等人將村集體資產(chǎn)非法占有,共同犯罪即構(gòu)成既遂。同時(shí),因?yàn)E用職權(quán)罪的犯罪主體為國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范疇小于國家工作人員,因此丙當(dāng)然不具備國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的身份。故丙違規(guī)分配保障房的行為更不構(gòu)成濫用職權(quán)罪。
四、共犯對罪名認(rèn)定的影響
第一種意見認(rèn)為,考慮到乙、甲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和行為,應(yīng)認(rèn)定二人構(gòu)成濫用職權(quán)罪共同犯罪,并對甲私自占有拆遷補(bǔ)償款的行為單獨(dú)評價(jià)為職務(wù)侵占罪。筆者不同意此意見。共同犯罪并不是為了解決共犯人成立什么罪名的問題,而是為了解決對共同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否都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的問題。換言之,共犯各參與人的罪名并非要完全一致。比如,在共同犯罪中,如果共犯中的部分人實(shí)施了轉(zhuǎn)化行為,導(dǎo)致犯罪性質(zhì)發(fā)生變化,而其中的部分人僅僅實(shí)施了轉(zhuǎn)化前的行為,同時(shí)對他人實(shí)施的轉(zhuǎn)化行為不知情,此時(shí),雖然成立共同犯罪,但也應(yīng)根據(jù)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確定罪名。
案例一中,甲、乙的違規(guī)行為共同導(dǎo)致500余萬元拆遷補(bǔ)償款的損失,二人行為與損害結(jié)果存在因果關(guān)系,均需對該筆損失承擔(dān)責(zé)任。因乙主觀上系違規(guī)決定以虛假材料騙取拆遷補(bǔ)償款用以補(bǔ)充B村集體資產(chǎn),并沒有非法占有該筆拆遷補(bǔ)償款的故意,因此,不應(yīng)認(rèn)定其構(gòu)成貪污罪,而應(yīng)以濫用職權(quán)罪論處。對甲來說,其在收到500余萬元后并未上交村委會(huì),而是私自支配使用,犯意發(fā)生了由濫用職權(quán)到貪污的轉(zhuǎn)變,應(yīng)將其行為作為一個(gè)整體評價(jià),按照貪污罪論處。
(李曌 作者單位:北京市朝陽區(qū)紀(jì)委監(jiān)委)
- 2025-06-30準(zhǔn)確識(shí)別以“商業(yè)機(jī)會(huì)”為幌子的權(quán)錢交易
- 2025-06-18職務(wù)犯罪案件中發(fā)現(xiàn)“自洗錢”問題后的監(jiān)檢銜接程序解析
- 2025-06-18單位受賄與受賄交織如何準(zhǔn)確認(rèn)定
- 2025-06-11國家工作人員與請托人互送大額財(cái)物如何定性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xué)習(xí)強(qiáng)國
學(xué)習(xí)強(qiáng)國 今日頭條號(hào)
今日頭條號(hào)